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 中华书局
作者:朱亦灵 著
出版:中华书局 2025.6
丛书:中华学术·近思
页数:404
定价:76.00 元
ISBN-13:9787101171440
ISBN-10:7101171443
去豆瓣看看 顺治三年春,在兄长因抗清罹难后,死里逃生的嘉定士绅侯岐曾始以“半生道人”之名作日记,“以备后人稽考”。透过日记观察侯岐曾“奉母保孤”的“遗民”生活,诗书游戏只是短暂的慰藉,与疟疾的抗争亦无成效。清廷的打击步步紧逼,侯岐曾竭力调度社交网络,却也无力改变大局。虽然心怀故国,他却对复明运动持谨慎态度,并无殉死决心。但最终精神趋于崩溃的侯岐曾还是卷入“松江之变”,家破人亡,成为明清易代史上又一幕悲剧。
本书引入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较完整地还原了晚明士绅真实的生命图像,展现了侯岐曾的求生渴望与赴死结局之间的张力,在学术理性之外亦饱含人文温情。
三、侯岐曾应对追索的策略
从结局来看,侯岐曾的诸般努力虽未实现免除籍没的预定目标,但绝非全无效果。倘若没有致以抚、督、县三方的多笔重赂与百般陈情,没有李雯、钱谦益等身在清廷的友人鼎力相助,清朝官府对侯家的籍没不可能再三延迟。侯岐曾作为乡绅拥有的人际网络与雄厚财力,是取得这一成就的基本条件。
(一)动用社会关系
侯岐曾动用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是向清朝官吏行贿,或通过亲友向其求情。行贿的本质是试图凭借与各级国家代理人建立起私人关系,回避制度约束,遂成为侯岐曾疏通清朝官吏的基本途径。侯岐曾对替他奔走的朱茂昭、夏平南等人也会致以路费与少许报酬,有时以“取酒”为名,数额在三五两到数十两白银之间,但向官吏行贿则是纯粹的权钱交易,金额也要大得多,如土国宝的幕宾沈弘之所得高达七百余两白银,知县杨之赋也在三百五十两以上。侯岐曾多少了解清朝的籍没政策,夏平南已为他打探到“守城原与死节不同,既尝取租,将来变产自难脱净”,在清廷身居高位的钱谦益也透露“守城殉节者籍,乃彼中画一之法”,一些朋友甚至与衙门胥吏都纷纷提醒他不要浪费金钱。但他仍不愿相信籍没与取租政策真的毫无通融空间,而是认为问题仅出在贿赂是否足量,或是否找对了有足够政治能量的受贿人。直到所有的贿赂都被证明无效,侯家的财力又几近枯竭,侯岐曾才开始尝试其他方法。
侯岐曾坚信行贿有效,原因之一是他既以“奉母保孤”为己任,面对家产籍没不可能坐以待毙。其二是他确实高估了私人关系影响官方制度的效力。与侯岐曾直接交涉的清朝官员主要是江宁巡抚土国宝与前后两任嘉定知县杨之赋、唐瑾,巡抚是决策者,知县系执行人。杨之赋在嘉定名声不佳,对侯家索求无厌,应出自个人操守的缺陷,但土国宝与唐瑾平素的施政风格与对侯家的态度存在显著不同。土国宝原为明朝将领,崇祯末年历任开州参将、河南总兵等职,顺治元年八月降清后,随豫亲王多铎大军南征。他军事才能突出,“熟闲弓马,深晓兵机”。次年闰六月江南抗清运动爆发后,土氏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成功镇压苏州府城的反剃发民变,并击退前来策应的前明江南副总兵吴志葵部。随即由都督武职改为文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七月加授江宁巡抚衔,开府苏州。明中叶督抚制度定型后,其职均由文官充任,清初则间用武将出身者。除土国宝外,尚有陕西总督孟乔芳、四川巡抚李国英、浙江总督张存仁等,多属清朝入关前就已归附的“辽人”群体。土国宝降清未满一年,资历尚浅,却一跃成为江南财赋重地的封疆首吏。又从武转文,违戾前明旧制,心不自安,便上疏请辞,结果被清廷驳回,证明土氏必有被清廷看重之处。土国宝任江宁巡抚六年,严厉镇压反清势力,但与愿意归顺的江南士绅也不无合作,政治手腕并不僵硬。知县唐瑾系清朝丙戌科新进士,在嘉定优礼绅衿,“日与诸生讲文艺,娓娓无倦色”,官声甚佳,名列县志《名宦传》。但这两位对江南士绅持温和态度的清朝官员对侯家却格外强硬,罕有通融,言行举止多肃杀之气。这表明他们的个人意志被官方制度压倒,清廷惩治抗清人士的决定势难调和。
夏完淳代侯家向李雯求情时,批评清朝的籍没政策反复无常,并无恒规。他提出同为死节之臣,前明詹事府少詹事徐汧与礼部侍郎管绍宁在殉国后并未被清廷没收家产,侯家却面临籍没之祸,实属不公。其实,徐、管二人与侯家的情况并不相同:徐汧在清廷颁布“剃发令”后就自沉殉发,管绍宁也因不愿剃发被官府腰斩,二人均未直接参与抗清活动,侯家则是组织地方士民抗清的领袖人物。从清廷的角度看,既有“守城殉节者籍”“守城原与死节不同”等成规,故籍没侯氏而放过徐、管,符合既定政策,并无不妥。夏完淳代友陈情,对侯家窘境多作张皇铺饰之语,自无不可,但所言毕竟不符实情。清朝官府对侯家籍没的态度忽宽忽严,朝令夕改,确属事实。但这源于具体经手的官吏受贿赂、人情影响而做出的一时妥协,清廷的籍没政策并未动摇,反而不断在隐显间“规正”基层官吏的举动,迫使他们对侯家持续施加压力。晚明士林与官场请托盛行、贪贿成风,使人情与贿赂能迅速“变现”为政治和社会资源,这是侯岐曾熟悉的行为模式。鼎革以后,侯岐曾察觉出清朝官场的贪贿之风依旧,却低估了清朝惩治反对者的意志与执行力,旧方法在新形势下难以收效就在情理之中了。
行贿之外,侯岐曾也多请亲友出面向清朝官府求情。正是由于姚宗典、李雯、钱谦益等人的先后介入,才使追索危机几度迎来转机,效果反大于一味行贿。还有许多亲友为侯岐曾四处奔走,打探消息,传递信件。倘无个人社会网络的帮助,侯岐曾可谓寸步难行。但侯家的社会关系在追索危机中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原因在于,清朝入关之初在朝中占据要津的势力是八旗贵族和北方士绅,江南官绅对中枢政治的影响力相对明末大为衰减。李雯与钱谦益作为江南籍官员,自身已退居权力边缘,无力撼动清朝对反清士绅的打击政策。侯岐曾等嘉定士绅虽以“四姓合局”“孝廉公觐”等方式试图自救,但只能对县衙产生些许影响,亦无助于挽回全局。 侯家的社会关系在明末足以扭转嘉定折漕事件的结果,入清后却不能免除自己的破家之祸,已预示了江南士绅在日后“江南三大案”中受清廷摧折的结局。
侯岐曾动用社会关系应对籍没,本质是运用一系列非正式手段与制度抗衡。他在过程中也善于利用官僚机构的弱点与制度自身存在的缝隙,如借助江宁巡抚衙门的申文向下级机构施压,以及试图阻止巡抚土国宝将籍没侯家之事具题上奏。对官僚机构与文书制度的熟悉,与体制内人员良好的私人关系,构成了他作为乡绅对抗国家制度的优势,创造出直接“从打结处解结”的条件,大抵为普通民众所不具备。但是,籍没手段自身的严厉性,与清廷有意借此惩治抗清人士家族的特殊背景,大大压缩了侯岐曾在制度框架内发挥社会关系的空间。另外,抚、督、县三方都可从不同的方式、程度上影响籍没结果,这在表面上给予了当事人某些钻营空间,实则迫使侯岐曾同时应对多个衙门,时刻担忧一环出错即前功尽弃,这也是杨之赋、沈弘之等人对他的肆意勒索总能成功的原因。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强调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使不同制度交叠一处,有助于民众自主选择通过何种制度获利,是“制度套利”的一种表现。但从侯岐曾籍没一案来看,多重官僚机构与国家制度的交叠一处给民间社会带来的亦不无恶果。
1.视角贴近生活,内容亲切活泼:
本书关注的是侯歧曾的日常生活细节,所讨论的许多事情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比如侯歧曾的下棋、打牌、听雨声等休闲活动,今人亦多有切身感受。侯家与疟疾等病魔的斗争,也会是许多读者熟悉的话题。侯歧曾为保全家产而不得不进行的违心交际,也会令读者会心一笑。
2.论世而后知人,文笔触动心灵:
本书富于情感关怀,文笔细腻入微,读来令人动容。作者深入而全面地展现了晚明江南的社会风气和文人面貌,并进而设身处地探讨了故事主人公侯歧曾的所思所为。侯歧曾这个热爱生活的人,在命运的捉弄下却不甘的死去,作者对其中荒谬与矛盾的勾勒令人不禁感到深切的同情。
3.固定模式,分析功力深厚:
作者对侯岐曾死亡历程的还原,揭露了侯岐曾勉力维持家族生存、重视生活情趣的一面,洗刷了过往记载中他“一心求死”的刻板形象。本书还运用了词语检索和统计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侯歧曾日记》,并引入医疗史和传播学的视角,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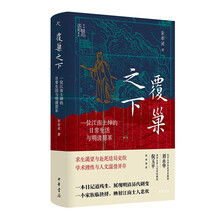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